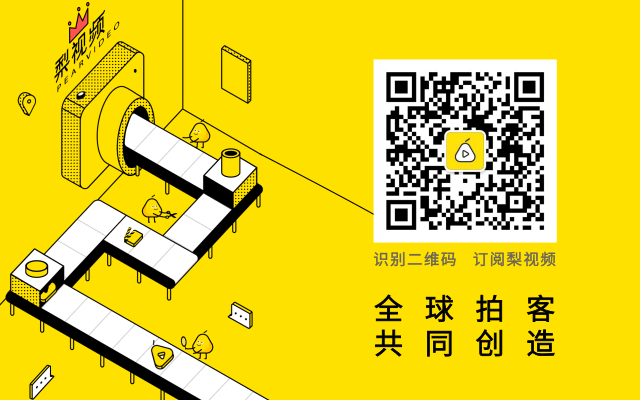近二三十年,辣椒和川菜就像是开挂的诸葛亮一样,《出师表》还没来得及写,就轻易统一了中国人的味觉。

按照前不久的一些数据,不仅传统上爱吃甜的苏州和上海都成了吃辣区,广东人的外卖新宠竟也是川菜。
辣这一火起来,西南地区的人们就突然多了一些别样的历史感,热衷于论证当地人吃辣史的源远流长,或者通过天气湿热需要祛湿来证明自己吃辣是注定的“天选之子”,黑他们的人则爱说,吃辣是因为物质匮乏。
从起源来看,这种说法可能没错,但并不是全部的真相。

我们之前说过,辣椒从明代中叶开始进入中国的第一个一百年,可以说是落寞的,飘忽于观赏花和药材之间。一直到康熙中叶,辣椒才开始进入中国人的饮食之中,但食用的地理范围仅限于贵州东部和湘黔交界的山区。
许多研究者都认为,贵州首先吃上辣椒,和当地缺盐有关系!因为中国人开始广泛吃辣的时间,已经是到了清嘉庆(1796—1820)年。当时中国人口从1亿左右猛增到了3亿,尽管玉米、红薯、土豆这一类的“美洲高产作物”有效支撑了人口爆炸,但按照曹雨在《中国食辣史》的说法,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农民将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种植主食,用于种植蔬菜等副食的土地随之迅速减少,“辣椒作为一种用地少,对土地要求低,产量高的调味副食到越来越多的小农青睐,这构成了辣椒在南方山区扩散的主要原因”。
可以说,没有那时人口爆炸,辣椒是不会这么快扩散于中国。
但直到20世纪初,即使在西南重辣地区,你仍然不能说吃辣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,因为,正是辣椒身上所附带的“物质匮乏基因”,决定了辣椒此时仍是一种难上大雅之堂的“庶民美食”。

以成都为例,迟至民国初年,餐馆里主打的味道还是“鲜香”,在1930年代著名的餐馆“姑姑筵”中,最流行的菜品还是开水白菜、樟茶鸭和蝴蝶海参这类菜。

学者蓝勇查阅了大量晚清的川菜菜谱,发现在两千五百多种菜品中,明确使用辣椒作为主要调料只有十几种,连1%都不到。
不过,蓝勇也认为,如果一味按照菜谱的逻辑,我们可能低估了清末民国时期辣椒对川菜的影响,不过有两点是基本肯定的:高档宴席是不太使用辣椒的;即使考虑乡村,清末民初的整体食辣程度还是相对较弱的。
也就是说,这些以辣为特征的经典川菜产生时间甚至比辣味流行还要晚近。比如,“川菜之王”回锅肉最早见于记载是光绪末年宣统元年;鱼香肉丝产生于民国初年;夫妻肺片产生于1930年代的成都街头;水煮肉片更是要晚至1960年左右才见于菜谱……

即使是川菜中历史可能最为“源远流长”的麻婆豆腐,也是要到1886年左右才开始出现。
其中最有意思的,可能是重庆火锅。尽管它最早源于清末的船工,但迟至1912年重庆第一家固定的火锅店才正式开业,店名叫“白乐天”。

到了20世纪40年代,火锅餐厅在重庆达到了高峰期,但尴尬的是,最有名的一家毛肚火锅竟然来自一家咖啡厅——汉宫咖啡厅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,重庆火锅才成名,之后很快横扫全国一发不可收拾。
吃辣最伟大的一次转折是,就是在这几十年,辣椒不仅从“长江中上重辣地区”征服全国,其间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之一,更神奇的是,辣椒从中下层民众的“匮乏时代的产物”,升级成为一种全民美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