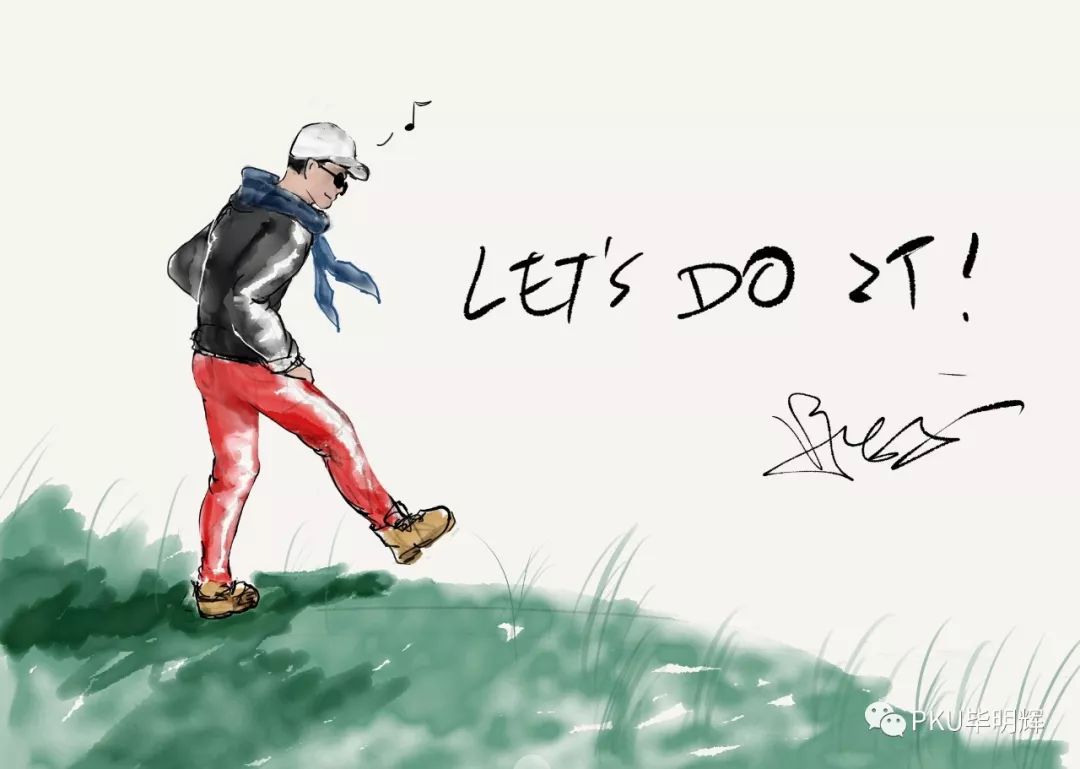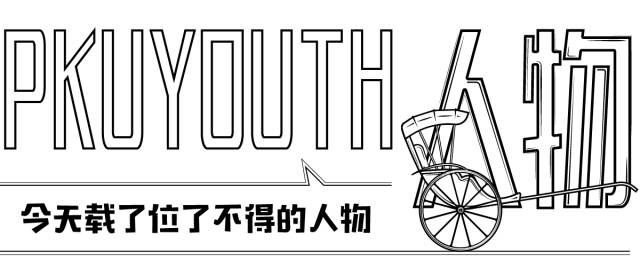
全文共4041字,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。
本报记者
金琪灵 公共教学部2017级本科生
杨红琳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
“死孩子们,又TMD都睡着了!都看着我!”
通选课《西方音乐欣赏》的讲台上,毕明辉老师敲着桌板,骤然提高的声音又一次把学生们炸了个猝不及防。
近五百人的大课堂上,兼顾全场的学生不仅困难,在许多人看来也没有必要,但毕明辉有自己的考虑。《西方音乐欣赏》的课后总结与通告里,他写:“我作为老师,无法放弃课堂里的任何一个人。无论你是在随我学习,还是在打游戏,我都别无选择。”
第一乐章 快板 Appassionato-热情地
2018年9月,《西方音乐欣赏》作为通选课第二次开课。从西方音乐历史上的七个阶段,到《卡农》背后的数理逻辑,短短两个小时的课程里干货满满。理教108的大教室里座无虚席,有的学生还搬来了教室外的沙发椅。
台上的毕明辉一身黑色,指着慕课视频里字正腔圆一本正经的自己抱怨:“这个人,我也不认识他。”但为了让学生们获得对西方音乐史完整的认识,他只好用上这段资料。

△
2018年春季《西方音乐欣赏》最后一节课前,毕明辉拍摄的理教108全景
在中国,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,基本都处在被忽视的边缘地位,“大部分时候,就是个唱歌课。”毕明辉所做的,则是给学生们补上缺位了十几年的基础音乐教育。
北大没有音乐本科,听课的学生大都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,但毕明辉很擅长深入浅出。讲节奏,他用中文自带的韵律来解释,“白日、依山、尽,就是三拍子”。贝多芬《命运交响曲》第一乐章著名的四音动机,表现的是残暴无情的命运,他有板有眼地唱:“你去死吧!”
虽然用词浅易,但课程的知识性却不因此减少。他给学生讲解蓝调音乐的十二小节行走低音,流行音乐抓耳的结构奥秘,交响乐第一乐章的奏鸣曲式,《白蛇传》戏曲里的润腔……古今中外,信手拈来。
学科交叉,是毕明辉讲课的另一大特点。他从音乐出发,可以联系到建筑、美术、文学,甚至数学、物理、信息。他用故宫的设计来解释音乐的空间,引用映射的概念来阐述旋律的变换,听课的学生大多都能从自己的专业背景、生活经历中,找到学习音乐的渠道和入口。
毕明辉对音乐的态度是工具主义,不空谈感觉,而是扎扎实实从音乐结构和组成入手,带着学生分析感觉来源于何处。“音乐是了解世界的工具,我的工作是给大家一套解开音乐内外奥秘的工具。”这样剖解音乐的方法,是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,还有他的那些故事。讲到世界各地的音乐,毕明辉常会话题一转,说起自己在那些地方经历的趣事:在埃及抽水烟,在卢浮宫看蒙娜丽莎,在北极办音乐节,“你们毕老师,地球绕了三圈儿了!”

△
毕明辉在秘鲁马丘比丘
讲肖邦的前奏曲时,毕明辉也讲了一个故事:他做国际义工时,曾在卢旺达遇到一个目睹自己哥哥身亡的小女孩,受惊吓得了失语症,一直哭不出来。义工团队里的人问他能不能做些什么,他就弹了一首肖邦刻画“泪滴”的协奏曲。听完,女孩哭了,两天以后就说话了。
他回忆,“做音乐的人,进校以后一路都是选手式训练,基本上已经剥离了对音乐美感最纯粹、最直觉的快乐。但在那个瞬间,我觉得学音乐还是挺好的。”
第二乐章 慢板 Dolce-柔和地
很小的时候,毕明辉就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。“我从小有一个梦想,像一个硬币的两面,一面是学音乐,另一面是当教师。有一天,我发现自己的梦想实现了,从此便非常快乐。”
他出生在军旅家庭,住的军区大院里有个很好的文工团。一旦文工团敲锣打鼓地要演出,毕明辉就跑过去看。上小学背书,他记得特别快,只要想一想豫剧《花木兰》的唱词,就能把《木兰辞》记个八九不离十。
小时候的毕明辉因为“长得好玩儿”,被抱上台做群众演员。那个时候起,他就决定要与舞台做朋友。对他而言,在音乐领域的最初启蒙,不是考级的功利逼迫,而是从小耳濡目染的自然萌生。
毕明辉觉得,“在一个方面发现了兴趣,正好能力又对得上,是一件很幸运的事”。他恰巧是这样的幸运儿,懵懂时就知道未来想走的路,也愿意为之拼尽全力地付出。
至于教师梦的由来,已不可考。在对职业、专业都一无所知的时候,毕明辉就告诉母亲:“我长大一定要当老师。”没有规划,没有目标,但他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愿望。
比起音乐,老师看似是一个更容易达到的目标,但其实,在这个职业广阔的可能性上,想要做得好却更难。怎样算是好老师,很难给出一个定义,毕明辉有的,只是一条条从经历中总结出的经验。
他小时候调皮,母亲脾气又急,受罚时,只记住挨揍的事,至于为什么要挨揍、母亲当时说了什么道理,一概全不记得。但在基地看露天电影时,母亲夸影片里帮厨师爷爷擦汗因此一路都有饭吃的小姑娘,一句“真有眼力见儿”,却让毕明辉记到现在。他因此而明白,“言传身教的的意义,永远胜过粗暴武力”。
博士后毕业之后,毕明辉到国外待了几年,还是决定回归做教育的本心。他在人人日志里自省:“本科毕业,不是没有工作,而是恐慌于拿什么教自己的学生。”本科毕业十年,他对自己的音乐能力已经足够自信,但说到能不能当个好教师,仍是抱着忐忑的未知。
2007年9月10日,阳光热烈。在这个教师节,毕明辉拿到了在北大的工作证。

△
2008年,毕明辉第一次在北大开设《20世纪西方音乐》课程
第三乐章 中快板,Abbandono-纵情地
十年前,北大的音乐教育条件并不理想:教钢琴的地方更像修钢琴的地方,图书馆里音乐方面的藏书少得可怜,教室里想听音乐没有音响,只能用中高频的扩音喇叭。
但比起硬件设施的缺乏,课堂气氛的冷漠,更让初来北大的毕明辉觉得不可思议。“课堂就是个流水席,上课,哗啦啦一大帮人来;下课,哗啦啦一大帮人走。”
在音乐学院的时候,老师都是一对一教学,师生关系特别密切,有很强的亲情感。毕明辉的恩师之一杨儒怀先生,每次听说他要来拜访都提前打电话询问确认,等毕明辉踏进他家门,茶几上必定备好一壶温度正好的咖啡。另一位恩师钟子林先生,给毕明辉发的祝福短信“新年快”让他一头雾水,先生随后来电话解释,原来是不会输入“乐”字。

△
2011年9月19日,钟子林出席《20世纪西方音乐·对谈龚琳娜》课程现场
如今到了北大,课堂大了,同学间都很少交流,师生之间更是难上加难。百人以上的通选课,课堂冷漠的现象尤其严重。当下与过去的鲜明反差,加上音乐学科在北大的边缘性质,让毕明辉在北大最初的两年,问了许多,也想了许多。
他把思考的结论写进日志:“教育是良心,不是股市,更不是关系。”学生和老师不是对等的,学生选了课,就有了要求教师的权力,而站在教师的角度,永远不能期望学生的回报。
北大过去没有合适的音响,毕明辉每节课扛着从美国带回来的Bose音响,像电影下乡一样去上课。《20世纪西方音乐》的五百份期末论文,他每份亲自看三遍,写成的阅卷回馈约有十几万字。2013年,这门课成了慕课,毕明辉在国外奔波之余,每讲上线时坚持写一篇开篇辞,介绍相关的音乐现象与文化。

△
《20世纪西方音乐》在北大停开后,毕明辉为选慕课的网络学生拍摄见面视频
除了课程相关,课下学生提的各种问题,毕明辉也都尽量帮忙解决。有次《西方音乐欣赏》下课,一群学生围上来,问他“大舌音怎么发”——那节课上他唱了意大利语歌曲《阿玛丽莉》,大舌音发音很标准。“这怎么也问我呢?”毕明辉无奈吐槽了一句,接着给他们解释起来。
他希望学生问问题要具体,“不要问我怎么听音乐,这就相当于问我,毕老师,我该怎么生活?你不如问,毕老师,我现在很郁闷,你跟我说说你郁闷的时候怎么办。”
学生便就依葫芦画瓢这么问他,他答:西门有个332路公交一直开到前门,一个人跑出去,坐在里面,转一圈,回北大。
第四乐章 快板 Brillante-辉煌地
毕明辉说:“北大,是个有光的地方。”有趣的是,他自己的名字,同光也有些关系。有学生用这个意象来做比喻:“包容而不放纵,陪伴而不代替,共情而不滥情。”
在“传道受业解惑”之外,毕老师的教育还有第四个原则:陪伴。音乐学院的教育风格,被他在北大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,他是“在孩子们累的时候给他们肩膀的人”,一个倾听者和理解者,一个分享故事的人。
听学生们说故事的时候,毕明辉对评价非常谨慎,“一个人是成就了自己,还是最终流逝了自己,现在都看不出来,还需要至少十年”。因此,学生们找他谈天时,他并不给出单向的价值判断,只从自己的经历中援引经验教训,平等分享。
在毕明辉眼中,每个孩子都是一件艺术品,而艺术品最高的价值,就在于不可替代。“父母给了他们完整,教育给了他们完善,完美是他自己的事。”
毕明辉很理解北大学生的心理:“很多时候,因为被预设要成为人中龙凤,他们的烦恼和困境要更多。”他爱把学生们叫做“丫头小子”,急起来就成了“大宝贝儿”,这样称呼并非单纯强调年龄的差异,而是因为他觉得,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。“人们常常认为,你都考上北大了,还能有什么烦恼,其实他们本质上还是个孩子。”
在北大中乐学社做指导教师的经历,尤其让他学会如何与孩子们相处。社团与课堂不同,师生间的关系更平等,他在中乐学社遇到的学生,都处在“最自然、最真实”的生命状态里。“中乐学社,其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,让我真正看到孩子们最本真无矫饰的那一面。”

△
毕明辉在百讲指挥中乐学社排练ACM-ICPC开幕式音乐会
2009年与中乐学社结缘,起初只是一种意外,但九年来,毕明辉与这个北大草根社团的关系,逐渐走向良性互补、互助、互需。中乐给了他课堂与学术之外的第三块试验田,让他对北大学生的了解更进一层,而中乐学社也在他的帮助下,成为了北大校园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笔。
2018年4月的ACM-ICPC开幕式音乐会,是他指挥的最后一场中乐学社演出。“中乐学社从来就不是我的,他们就是他们自己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”对自己班上毕业的学生们,他的态度也十分淡然:“意义往往都需要时间的积累,才会慢慢凸显,感伤最终只是一种点缀性的装饰。”
他带过的两届学生都已毕业,如今第三次当了班主任,许多中乐学社的孩子们,也已各奔东西。学生们记不记得他,回不回来看他,毕明辉都不在意:“尽力而为,适可而止。尽兴地与学生擦肩而过,这是教师的宿命。”
尾声
毕老师自认,他这个人没什么好写的,采访来采访去,都脱不开那几句话。“就差问,毕老师你怎么保养的,怎么这么多年都不变样?”他笑,“我觉得有两个原因,第一,音乐,第二,学生!”
图1、2、3、5来源于受访者,图6来源于李倩茜,图4及封面来源于网络
微信编辑|周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