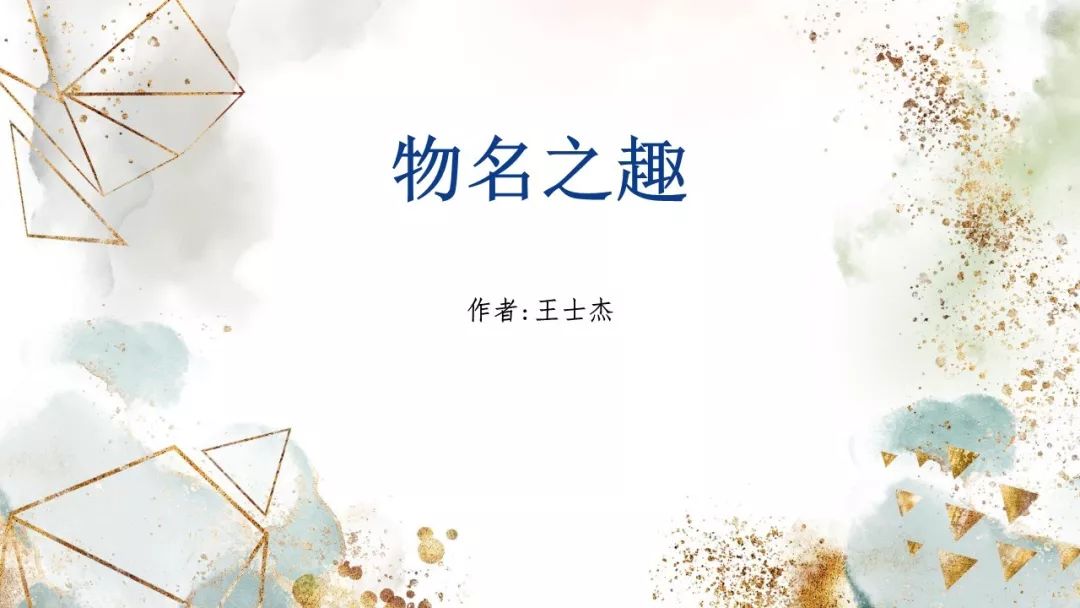
地域相异而物产有所不同,此有彼无,或者此无彼有,物名也就因地而异。这是“一方之物”决定“一方之言”,引人关注的自然是“物”:人家那儿有,而我们这儿没有,这东西稀罕!另一番情形则是,同一种东西、同一类事物,却异地异名、各说各的。这是以“一方之言”来说“通常之物”,引人兴趣的无疑是“言”:他说的与俺说的不一样,怪有趣的!有朋自远方来,或者涉足异乡为异客,谈笑间,我们发现各地的方言竟是那么丰富多彩、那么异趣横生。在双方惊讶好奇的寻问与“对译”中,才知道自己说惯听熟了的那些“物名”原来还有别的说法,而且各具特色、耐人寻味。可惜我们之中能够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人并不太多,即使属于“不太多”之列,对各地的方言也很难做到“百晓”如“万宝全书”。在普通话(标准语)绝对强势的语境下,媒体如电视、网络虽不时有方言俗语精彩呈现,却难成气候。处一隅而欲领略诸多方言之风采,其实很难。正因见闻有限,“物名之趣”这篇文章恐怕只好“倒转来”做:先以自家方言为例,抛砖引玉,再请各路朋友各“晒”其“言”,彼此分享各地话语之趣,岂不蛮有意思?那就先以我们桐乡方言为例,来跟普通话作一个对比(每组后者为桐乡话):虾——弯转;蜈蚣——百脚;蚱蜢——谷蜢;毛毛虫——蛓毛;蜗牛——驼包蜒蚰;蝈蝈——叫呱呱;蝉(黑色而长鸣者)——老钳;蝉(绿色、鸣而成调者)——夏知调;黄颡鱼——汪钉头;河蚌——水菜;青蛙——田鸡;春笋——毛针;豇豆——裙带豆;桑葚——乌嘟;豌豆——寒豆;南瓜——饭瓜;午饭——点心;点心——小点心;菜肴——小菜;鞭炮——百响;火柴——自来火;卫生纸——糙纸;缝衣针——引线;左手——借手;右手——顺手;腋下——勒克子;膝盖——膝钵头;翅膀——节拐;细雨——蓬花雨;旋风——鬼头风;虚年龄——叫名;礼金——人情……方言给事物起名儿,颇有点“自说自话”,但细细品味却又“自有道理”。“这样说”而非“那样说”是有一定理据的。比如,“虾”之所以称之为“弯转”,是因它烧熟后“弯腰拱背”的形状。“蜈蚣”称之为“百脚”是因为它的脚实在是多。“蜗牛”则更有趣,外观上很像“背着包的蜒蚰”。而“春笋”、“豇豆”、“桑葚”,也都因其形状或颜色而分别称之为“毛针”、“裙带豆”、“乌嘟”。而称“豌豆”为“寒豆”,则因其为越冬作物,冬去春来才采食之故。至于“百响”、“引线”、“顺手”、“借手”之类,皆缘其功能而命名。只有“点心”(午饭)、“小点心”(通常所说的点心)之称有点费解,为啥这么说?只能推测:农耕社会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农忙之际抢收抢种时不我待,午饭常来不及准备更无时间细嚼慢咽,只能马虎吃一点垫垫饥,所以称午饭为“点心”。至于一般而言的点心,那只能算是“小点心”了。大家已经看出,同样的物名,普通话侧重于揭示事物的概念而显得理性,又多源自古代书面语而显得典雅;方言的表述,则更直接地关注事物的形态、色彩、声响、味道、功用等,因而显得感性,显得随俗,更口语化,更生动有趣。有意思的是,因地理环境、风土人情、观察视角和语言习惯的差别,不同方言对同一事物的表述,往往各显异彩。例如:(1)蟾蜍——癞癞嘟(东北方言)——癞疙宝(四川方言)——癞呱呱(兰州方言)——癞太婆(桐乡方言)(2)蜻蜓——蚂螂(东北方言)——丁丁猫儿(四川方言)——春官(兰州方言)(3)蝙蝠——燕蝙蝠(北京方言)——燕别古(东北方言)——檐老鼠儿(四川方言)(4)蟋蟀——蛐蛐儿(北京方言)——错翅子(兰州方言)——蟮唧(桐乡方言)(5)膝盖——拨棱盖儿(北京方言)——玻了盖儿(东北方言)——勃膝盖子(兰州方言)——膝钵头(桐乡方言)(6)风筝——风登儿(四川方言)——鹞子(桐乡方言)……正是这争奇斗艳的南腔北调,赋予了各方话语奇特魅力,给跨地区文化交流带来了无尽乐趣。那些过分强调方言对交流的不便与阻隔,过于强调规范化、标准化,以致主张遏制方言,举国一调的观点,多么狭隘,多么片面。方言与普通话应该互为表里,共存共赢。除非正式场合、公众交际、学业考试之必须,咱们不妨多讲讲家乡土话,多说说小辰光奶奶、外婆常絮叨的那些词儿。在乡音母语的陪伴下,把“根”留住,把“话”传下去。
